深圳之佛塔
塔,原為佛教僧尼的墓塋。按印度風俗,人死後習慣行火葬禮。當年佛祖圓寂,遺體火化後由弟子拾撿遺骨舍利,埋於土堆,蓋以磚石,形若覆碗,梵語稱為窣堵坡,漢譯為「佛塔」。據傳參禮佛塔,如親見佛,可得福蔭。
佛教傳入中國後,僧尼沿襲傳統,多在寺院後山建造骨塔。後來受到我國建築技術影響,塔的形制改向高空發展,甚至由全實心的柱狀塔進化成樓臺式的高塔。唐代以後,皇室與官商流行建造佛塔,藉建塔功德祈求佛佑。風氣所及,民間信徒亦習慣在交通要道建造小型佛塔,既為積累功德,亦祈出入平安。
考香港之九龍海(維多利亞港),於宋代已為重要船泊補給點。近數十年間,維港兩岸先後出土宋代遺址,包括錢幣及貨物,並有大型村落建置。更重要是西貢佛堂洲曾出土宋代稅關遺蹟和文物,而該處之東面大廟灣後山遺留南宋咸淳年間(1274年)石刻,文云:「古汴嚴益彰,官是場,同三山何天覺來游兩山。攷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文中明確指出在南佛堂(即今東龍島)於北宋真宗期間(1012年)建造石塔一座,其位置在維港東邊出口不遠。可惜,至今尚未發現古塔的確實位置,可能已毀於風雨,又或只隱沒於叢林,等待發掘亦未可知。對此,史學家曾作若干考究,更提出不同的論點,惟至今仍無定論。
由禁醮說到茂峰法師的社交
在整理茂峰法師的資料時,往往發現茂公與許多廣東的官紳人士時有往來,這固然與法師的德行有關,其實也與民初時期,政府實施「禁醮」的歷史背景有關,因此也略為補充說明。
辛亥革命前後,知識分子倡導西學,一時之間全國瀰漫「全盤西化」的風氣,往往認為傳統文化是落後,更視佛道信仰為迷信,對於坊眾啟建宗教醮會(法會)最為鄙視,認為是散播迷信,愚昧民智的行為。當時,廣東地區政府已陸續禁醮。後來,教育部更通令全國取締。但民國建國以來,國家並未得到和平,各省軍閥劃地為王,經常為土地利益而發動戰事,軍民傷亡自然不能避免。站在軍官的角度,每次戰事均有傷亡,超度陣亡將士並藉此安撫士氣民心最為重要,於是形成文官反對打醮,武官推動建醮的特殊狀態。
雖然國內不便打醮,但香港因屬殖民地,政府不干擾宗教活動,華人可自由舉辦醮會,也間接推動了本地市區的弘法活動,經會、法會相當興旺,於是也雲集許多的高僧大德。其時,廣東作為北伐基地,軍事活動頻繁,軍官對建醮有實際需要,但中央政府既有禁令,信仰佛教的軍官多以講經活動附帶進行祈福活動,但一時三刻也難以找到合適的高僧主持。適值年輕的茂峰法師由台灣返回大陸,過境香港時獲本地居士邀請留港發展。茂公是廣西人,通曉粵語,且年輕有為,德行高潔,先後獲圓瑛法師、諦閑法師等大德賞識讚譽。加上曾到江南留學,又到過台灣任教佛學院,頗有聲譽,正是不可多得的人材。
道慈佛社張祝珊小學
日前應邀參與「道慈佛社張祝珊第二小學的周年晚宴」,當晚筵開三十多席,共四百多位的師生聚首一堂,暢談往事,細閱舊照,追憶當年的生活點滴,許多已榮升祖父母的校友,也頓時返老還童,表現童真的一面,我置身其中,聽着師友們細說從前,也感受到那種筆墨難以表達的感情,實在很溫馨,我也值此介紹張祝珊學校的沿革,補充一點背景資訊。
張祝珊學校由道慈佛社主辦,該社於1944年由楊日霖等本地商人成立,會董均是社會賢達,除了弘法外也組織救濟及文化活動,其中以長年舉辦慶祝母親節及父親節大會最受社會矚目和讚賞。
五十年代末,因應人口及經濟持續發展,適齡學童對教育需要有增無減,而佛教人士經多番努力,成功爭取開辦政府津貼的學校。當時,佛社邀請到時任東華三院主席的張玉麟居士擔任董事長,積極推動佛社增辦教育項目。
張玉麟居士,是張祝珊老先生的公子,早年協助家族經營籐器業務,戰時與母親來港定居。後來,家族轉營代理西藥而致富。張居士與夫人一向熱心公益,屢任本港商會及福利單位領導,1960年更任東華三院主席,有聲於時。當他擔任道慈佛社董事長,隨即邀同母親及胞弟捐款辦學,成就了會屬多所學校。
澳門功德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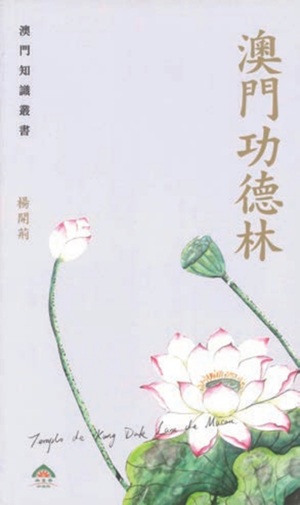
《澳門功德林》
這次香港書展期間出版了一本好書,就是澳門楊開荊博士編著的《澳門功德林》,本書不但簡介佛寺的成立和沿革,也從新發掘功德林的事業與當時港澳社會的互動,更重要是楊博士的團隊用了十多年時間整理寺內數千冊的文獻文物,並成功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是港澳台地區唯一與佛教有關,並成功「登錄」的案例,意義極為重大。
敬悼兩位法師

慈靄的了知法師
2017年已過一半,對有兩位大德往生,甚為惋惜,這分別是東普陀寺的了知法師和鹿野苑的超塵老法師。
了知法師是廣東恩平人,1947年來港。那時正值內戰,無論僧尼或是尋常百姓,只要有能力的都想逃到香港避戰,而東普陀寺的茂峰法師感念災民遍野,胞歷悽愴,因而大開方便,接引僧俗難民,來者不拒,了知法師也在這種背景下來到東普陀寺,翌年依止茂公出家,法號了知,字聖慈,這時剛好二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