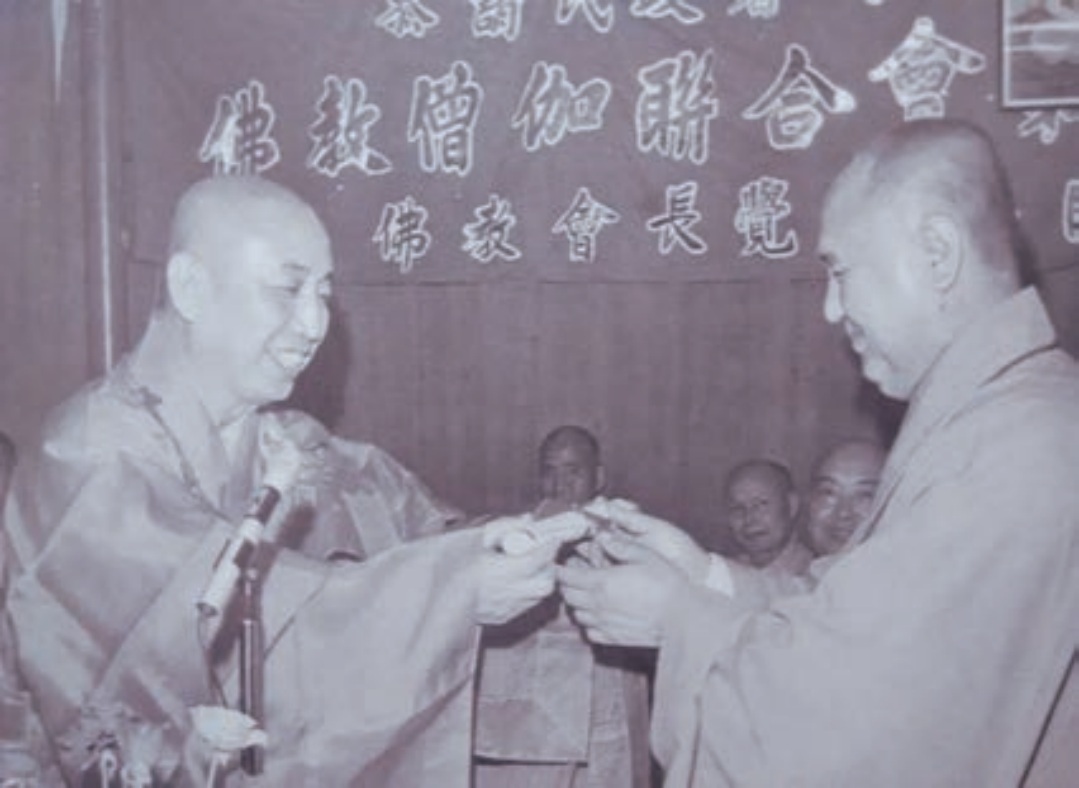廣東一帶,因粵北大庾嶺山脈的阻擋,氣候與文化均自成一角,形成獨特的「嶺南文化」,在這種氛圍之下,廣東佛教的儀規禮俗亦有別於江南、華北等地。
自唐宋以來,廣州與潮州因位處海路交通要道,已是嶺南地區的佛教傳播中心。不過說到具規模的戒壇,則以粵東羅浮山延祥法脈的華首臺寺和粵西鼎湖山曹洞法脈的慶雲寺為代表。可想而知,兩廣地區出家的沙彌須到其中一所戒壇受戒以圓滿僧籍,兩所戒壇自然成為培養僧材的重鎮。
清末民初時期,來自西江一帶縣市和廣西的法師均到鼎湖山參學,適值華南戰亂不休,鄉郊地區治安不靖,寺院往往成為賊匪「打主意」的對象。此外,國家的「廟產興學」政策,以法令的形式直接沒收寺院財政,也對叢林做成打擊。有見及此,不少年輕學僧紛紛往江南參學,一方面減輕對寺院的負擔,同時藉着參訪雲遊增廣閱歷,於修行亦有裨益。
其時,在鼎湖山參學供職的學僧包括茂峰、茂蕊、筏可、融秋、增秀、靈溪、遠參等十多位法師,他們結伴到江南參訪,有的到鎮江金山寺,有的到常州天寧寺,總之雲水隨緣。經過數年參訪,部分回到鼎湖,輾轉再到香港,隨緣弘法。
二十年代,筏可法師、靈溪法師、暢緣法師、精參法師及本覺法師,五位故友更不約而同來到大嶼山,開展弘法事業。
暢緣法師,原籍廣西。1926年來到東涌後山,發現在天然石洞,在此隱修,七十年代才擴充為羅漢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