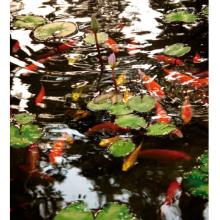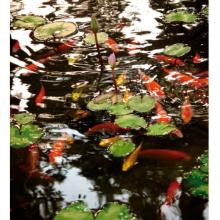東北三老與弘法精舍
故事該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講起 ……
「弘法精舍」緣起
一九三八年,香港商人黃杰雲購入青山公路九咪半地段,建造精舍供三夫人王壁娥靜修。翌年,天台宗寶靜大和尚從寧波觀宗寺到香港弘法。黃杰雲、王壁娥夫婦、李素發、王學仁及林楞真幾位居士發心,請寶靜大和尚長駐香港弘法利生,並將剛建成的精舍命名為「弘法精舍」,邀請寶靜大和尚於此創辦「弘法精舍佛學院」。
寶靜大和尚為此特別從寧波觀宗寺招收了青年學僧 十餘人到港深造,當中包括了今日香港佛教領袖覺光長老,又在廣東一帶招收了二十名學僧。寶靜大和尚擔任院長兼主講外,又邀請了廣東的寶乘法師、東北的化東法師為學僧授課。課程有天台教觀、戒律行儀等,是為香港近代教育之發軔( 圖一)。